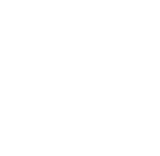You are here
Lena Scheen
近一期的教师午餐交流会,聚焦在浦东地区的一个建筑工地上,那块地上曾经有一座500年历史的寺庙。演讲者告诉大家,现在仍有一些老人到建筑工地围墙外祈祷和焚香。对这块地方的研究过程中,见闻到很多故事,令这位演讲者十分着迷。我们对演讲者做了如下采访:
请您简单地介绍一下自己吧。
我叫Lena Scheen。从2012年8月,也就是自上海纽约大学在上海成立起,我就在这里工作了。我教的课程有:上海近百年来的小说、上海城市发展,还有上海和底特律城市发展的比较。最近刚刚出版了一本关于上海现代文学的书,叫做《上海文学想象:一个转型中的城市》。
讲座中听到关于你对于你的研究的描述,让我想到了讲故事,感觉你的很多工作都是围绕着讲故事展开的。
的确是这样。我对讲故事非常感兴趣。故事是我研究的源头,我探索上海快速的城市化对于个人和社会的影响。我着眼于研究故事是如何书写变化中的城市的,以及故事中的这些想象如何表达近期变革的精神和社会影响力。为此,我不区分虚构的故事、政府或媒体上官方的故事、城市传说、口口相传的历史,或者是个人和家庭的故事,我相信所有这些故事不仅仅反映或是投射了变化中的城市,更重要的是他们本来就是城市变革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演讲提到的这个研究项目,就是着眼于浦东的这个建筑工地上的小说故事和历史故事。所以,的确,讲故事绝对是贯穿我研究的一条主线。
这就使得中国成为了一个值得研究的有意思的地方,对吗?比如,文化大革命抹去了很多的故事,或者说使一些故事变得更加重要了。
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实际上,文化大革命在于它在中国的历史上创造了一个“黑洞”。但是由于那段历史不在那,却使得它更在那。用王安忆的一部小说 《长恨歌 》来举个例子,人们说“好吧,她很大程度上略过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描写”。但是实际上,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那些年某种程度上来说被跳过去了的这个事实,使得那些年仍一直存在于当下。我在很多的小说中都看到了这一点。有意思的是,文化大革命曾试图通过清除“四旧”抹去历史,而现在,文化大革命本身就被历史抹去了,这是集体失忆。然而,它就存在于历史的缺席中。事实上,有很多以文化大革命为主题的小说。现在,隔着时间的距离,我们看到很多人重新讲述文化大革命的故事。故事被抹去,然后被新的故事替代,这就是历史。
“它就存在于历史的缺席中”,这和你讲座中那座庙的情况类似,建筑工地在,但是庙已经不存在了。
是这样的。寺庙的实体已经不在那了,但是人们仍去那儿祈祷,使得寺庙仿佛还存在于当下。如果你去那儿,你能看见的就是一堵白墙,上面写着一些字,围着那个建筑工地,地上有一个大泥坑。这不能算是一个地方,直到有了故事,才能成为一个地方。所有的故事都源自于地上的这个大泥坑。这正是这个地方如此有意义的原因!你站在这个大坑前面,除了围着它的墙,其他什么都没有,但突然这“什么都没有”的坑变成了一个盛满了所有这些故事的大容器:个人的故事、国家的故事、国家的故事、还有神话。
如果一个地方有着非常清楚的定位,比如老城区的豫园,能看到那些优美的结构 - 九曲桥、老茶园、城隍庙 ,那些历史就都清晰地呈现在你眼前。你知道豫园曾经坐落在城市的中心,知道它存在的时间,知道那些建筑都是做什么用的。当你在那里的时候,你能很清楚的知道你在哪儿。对我来说,那一点都不好玩,因为太直观了。然而,当你站在一个环绕着建筑工地的白墙面前时,你认为那里什么都没有,但正是因为它没有被定义,或者说没有既定的概念,它才能由此对所有的故事敞开。
你的意思是像豫园一样的地方,由于已经有了自己的品牌或者说是明确传递的信息,就会掩盖很多其他的故事吗?
是的,你说的太对了!我确信与豫园相关的很多吸引人的故事和城隍庙、茶园,或者其他我们知道的和豫园相关的东西无关。但是那些故事都太难被发现了,因为豫园是一个已然被清晰定义的一个地方。反之,这构成了浦东的这个寺庙旧址吸引我的原因。我认为一个地方第一眼看上去没什么意义的话,反而会促使你真正看向其中,并且能够发现日常里不会发现的一些情况。当我看向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没有任何的先入为主的概念。我只是恰好路过,并且问我自己“这儿发生了什么?”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会最终成为我的一个研究项目。我只是单纯的好奇而已,是这个地方本身给我讲述了这些故事。它一直在给我讲故事。我有时觉得这个城市正在对我诉说着故事,我所需要做的就是倾听。
这个地方带给你兴奋还是沮丧呢?
哦,这个地方不断地让我着迷。通常科学家或者学术研究者初次了解了一个话题之后,可能就会深深地痴迷于那个话题。我是一个可能对任何事情产生兴趣的人。我经常被一些随机出现的,或者第一眼觉得很无聊,但是后来发现很有趣的事情所吸引。
如果你真的深入了解,任何事物都可以非常迷人。比如你看这个瓶盖(指向一瓶矿泉水的红色瓶盖),它没什么特别的。但是如果你想,世界上所有的瓶盖都是一样的,这难道不神奇吗?世界上其他的地方也使用这种旋转的瓶盖。其实一定有其他的方法盖住瓶子,但是我们都在用这一种!然后我就想,他们是什么时候开始用这个方法的呢?是谁设计出来的呢?人们现在有在研发新的方法吗?我还会问,瓶盖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呢?这些塑料都是哪里来的呢?我们把它扔了以后会怎么样呢?这样就又转换到了环境话题,就又是一个全新的有趣的领域了。
让仍旧去寺庙旧址的老人们讲故事容易吗?
当然不容易。正如我说的那样,一开始我不知道自己会把它变成一个研究项目。我被这个地方迷住了,于是越来越频繁的去拜访那些老人。他们告诉我的故事越多,我就越感兴趣。这时我意识到了这可以成为一个研究项目。为了开始我的实际研究,我必须了解他们,他们也需要了解我。我每个月特地安排三到四次和他们的聚会。如果你们无法建立信任,人们就不会把所有的都告诉你。人都是有弱点的,而这些故事都是围绕着人的弱点的,你必须正视这一点。
如果你想知道他们的故事,你就得先给他们讲你的故事,是吗?
是的,我认为是这样的。做研究就是,与研究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对研究持有清晰的目的,但是当涉及到人类研究时,当你和人打交道的时候,需要把自己也带入其中。不能否认我是一个想知道他们故事的欧洲白人。如果我是上海人,一切就会很不一样。他们和我说话的方式、我如何看待他们、我的研究方式,我怎么写,都由于我是一个欧洲的学者而显得很不一样。
而最重要的是,我期待他们对我敞开心怀讲述他们的故事,我也应该告诉他们我的故事。我认为这是尊重别人的故事的唯一方式。他们是活着的,这是他们的日常生活,这是他们非常在意的事情。他们当然会敏感和焦虑。有时愤怒,有时悲伤,有时快乐。如果我不分享我的故事,他们就不会信任我,我也不会感到好受的。这意味着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来建立关系。我从去年三月开始就一直在和他们接触,还没有开始正式采访。
从别人那里要钱比从别人那里得到一个故事要难得多,你同意吗?
是的,是这样的。这不是一项交易。你不能说“我给你甲,你给我乙。”唯一使人自发地、发自内心地讲述他们故事的方法就是赢得他们的信任,并且懂得如何去倾听。
这个过程教会了你同理心?
是的,这需要同理心和时间。有时你遇见一个人,第一晚你就可以告诉他,你一生所有的故事。那是两个人之间产生的化学反应。但大多数的时候只有你了解最久的那些人,你的家庭和朋友才会对你敞开心怀。在我遇到的很多人眼里,他们认为我是一个“美国人”,“有钱”,“有名“,“厉害”。我花了很长的时间说服他们,我不是他们认为的那个样子。我不是美国人,我也不是他们认为的那种很厉害的人。他们特地对我说“你就不能给荷兰大使馆打电话告诉他们,我们需要重建这个庙吗?”,我说“事情不是这样的,即使我非常有厉害,也不能就直接打电话去荷兰大使馆。即使是荷兰大使馆也没有那样的权利!”
你是如何说服学生们关于寺庙旧址的故事是很重要的呢?
我试着不告诉学生们为什么一件事情很有趣或者很重要。我不认为他们应该要对什么事情感兴趣。我问他们一些问题,激发他们思考为什么某件事情可以很有趣,同时,我教他们能够找到答案的各种方法。只有他们自己试着寻找过答案,才能自己判断究竟这件事情重不重要。
我带过一个班的学生去过那个寺庙的旧址。当我们站在手写的“这里曾经是七甲(音译)寺”的墙边时,看着地上的蜡烛和香焚烧过的痕迹,我问学生们一些问题,比如“地上的那些痕迹是什么?“,”看着这面墙的时候,你想到了什么?“,“你认为谁在墙上写的这些字?”, ”为什么他们要那么做呢?“。 于是他们就开始猜啊猜。他们开始编故事。然后我才告诉他们关于这个地方的情况。那时他们就已经上钩了,他们真的很想知道答案。
在你引起了学生们的好奇心之后,就更容易说服他们某件事情很重要了。通过回答关于这个地方的一些问题,他们从这座寺庙和它后面那座教堂的故事里,学习到了关于浦东的宗教历史,了解到了这座寺庙是为了纪念明代抗倭将军戚继光而建的,还有著名的共产党特工李白是在这座寺庙前被杀害的。同时,他们也了解到了浦东的城市发展变化。这个看上去很随意的地方有那么丰富的历史。我希望这些历史能让他们意识到这里的重要性。这也就是我在教师午餐交流会上所讲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