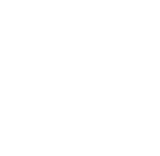You are here
Andrea Jones-Rooy
能请您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您自己吗?
我是Andrea,我是全球中国研究的助理教授。我的研究领域和教学方向是政治科学。我在上海纽约大学教授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学。此前,我在密歇根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在美国学习期间我学习了独裁政权利用媒体的方式以及它是如何影响国际关系的。我的研究主要是关于媒体在政治领域里的角色,中国正是我毕业论文里面的一个案例。
我在上海纽约大学研究审查制度。下个学期,我将教授比较政治学。我们将对比不同的体制,探讨每个体制相对其他体制好的一面和落后的一面。我们将站在一个完全中立的立场上思考。美国人总是很容易有“民主政治是完美的,其他的体制都有很严重的缺陷“这样的偏见,但民主政治也是有很多问题的。我们的想法是,作为科学家,我们能否找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我们能否得出“在一个国家行得通的方式在另一个国家也能行得通”这样的结论?这就是我们在上海纽约大学一直以来的对话基调。
您的全球中国研究都包含哪些议题?
全球中国研究是国际关系和东亚研究的一个结合。我们不是让学生们去学习一个单纯聚焦在中国本身的项目,而是把国际关系也融合了进来。因此,我们的想法是国际中国关系研究不仅要让学生们了解中国的情况,同时也让学生们对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世界如何影响中国、以及中国如何影响世界等等也有一定的了解。
因为这个专业在世界上其他地方都没有开设过,所以同学们难免有些焦虑。他们不知道如何跟他们的朋友们解释这个专业。我认为这个专业非常有价值,因为关于中国的研究和教学常常会进入一个只讨论中国的困境。所有的一切都聚焦在中国本身,不会考虑外在的因素。即使是高水平的学者也很少会将中国与世界其他的国家联系到一起。世界的其他国家仍以美国为中心运转着,常常忽略了中国。理论上来讲,这个专业是一次合并两者的机会。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对于上海纽约大学来说是一个完美的专业,因为这就是这所大学的全部意义 – 进行改革创新。
您能讲讲教职工午餐讲座吗?您是如何想到这个主意的?
从根本上说,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参加过的最棒的社团就是复杂系统研究中心,那是我所知道的最成功的一个跨学科的项目。物理学家们会和经济学家们还有政治学家们坐在一起。我们会谈论我们所研究的问题的共通的部分,那种感觉很奇妙。我并不是总能理解那些科学家们谈论的所有的东西,但是能看到其他的科学家和人文学教授们是如何思考的仍然是一件非常酷的事情。我只是喜欢知道其他人都在干什么的感觉。
我离开了自己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的任职来到这里,我是以一个博士后的身份过来的,所以这连升职都算不上。我答应来上海纽约大学的一个原因是我在纽约遇到了Joanna Waley-Cohen, 她告诉我上海纽约大学没有部门。2014年我们的团队如此的小,只有30名教员。Joanna是一个历史学家,她告诉我她经常和生物学家还有工程师们聊天。我喜欢学习各种各样的事物,所以我认为那实在是太棒了,因为那就是研究生院我最喜欢的一点。
我刚到上海纽约大学的时候,每个人都在不同的楼里工作,因此很难有机会去认识其他的人。于是我去找Joanna提议举办一个每周性的讲座,从不同的领域邀请一个人在比较轻松的环境下讲讲他们在做什么。我们最近刚刚以一种不是很正式的方式开始了这个讲座。我们的第一个演讲者是人文科学的Lena,所有的经济学家都问了她问题,比如“为什么你不用数据?” 她对这些问题都回答的很好,她说“你无法用数字精彩地讲故事”。
这个学校最好的一点是我们有这么多跨学科的、闻所未闻的专业。学生们有时觉得这和他们想象中的大学不太吻合,但是我反而认为这很棒。如果四年以后学生变成了一个真正有趣的人,那么我们就成功了。如果你来自上海纽约大学,你会有很多可以讲的故事。任何一个简历上面有上海纽约大学的人都将被潜在雇主多关注一些,他们一定对我们的学生充满了好奇。
由于我工作的原因,我和很多学生都交谈过,我充分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一开始我以为是巧合,我以为我只是很幸运地恰好选到了那些既有趣又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学生进行采访,但随后我意识到和我交谈的每一个学生都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融入了学校社区和这个城市当中。他们会去剧院,也做很多其他有趣的事情。
是的,如你所见,我的办公室里有一大堆的艺术品。我给学生们布置的一个额外加分的作业是“根据课堂上的学习资料画一幅画,我就会给你额外的分数”。他们所有的人都做了这个作业!我本来以为能有几张纸收上来就很好了,但是他们做了卷轴、巨大的海报,甚至还有剪纸作品。他们热情似火,来自不同的国家。他们也许在瑞典长大,又在非洲和南美洲生活过。他们能说十种语言。他们已经比我聪明了。
谈到在上海市这个大社区环境里激动人心的活动,您能讲述一下您是如何加入太阳马戏团的吗?
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就进入了马戏团。我从小就是一名舞者,在大学期间的辅修是舞蹈。我进入研究生学校就读之后就暂时放下了舞蹈,试图认真地专注于学术学习,但是随后我发现这使我感到很无聊。我不喜欢去体育馆,所以也没有做任何的体育锻炼。直到后来我在底特律的一个仓库里找到了一个工作室,里面有很多的马戏团道具,于是我开始利用星期日参加一些关于丝带和秋千飞人的课程。我来中国之前的整个夏天,我都很努力地在纽约进行练习。到了中国以后,我担心自己可能又要落下训练了。一两个月过去以后,我觉得自己被这个想法弄得坐立难安,于是开始找地方上相关的课程,恰好发现太阳马戏团要开张了,于是我就去试演,最后他们录取了我。
最后一个问题:您在这儿拥有的最好的回忆是什么?
我在想一件今天发生的事情。对于我课堂上所有的考试,我的原则是学生获得的最高分就是满分。因此如果学生得到的最高分是95分,那么95分就变成了100分,每个人的分数就都有一个提升。我们在课堂上研究合作和集体行为。自我给他们上课开始,我就告诉我的学生们如果每个人考试中都得了50分,那么50分就是新的100分。如此,如果你遵循这个规则去推导结论的话,如果每个人都同意交白卷,那么每个人就都能得100分了,但是如果一个人回答了一道问题,那么其他所有的人就都不及格了。我在卡耐基梅隆对学生们提出过这个挑战,没有一个班级的学生按这个方法得到过全班满分,但是今天,我在上海纽约大学的班级做到了。
确切说来,我的学生们实际上并没有参加期末考试,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使得他们完成这个挑战的前提是他们必须将关于国际合作的所有的概念都消化学习好。我们讨论了在每个人都有动机打破协议的情况下如何让几个国家同意一个条约,或者停火,或者是解除武装力量。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谈论为什么像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这种两国间的条约总是失败。我认为如果我们将已经消化吸收了这些概念的学生们送去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一定将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我的希望是他们将永远记住这次考试,即使他们也许不会记得住一些他们真的回答了的考试。
在上海纽约大学我们总是说我们是先锋,我们在做的所有的事都是创新的事,而这也正是我喜欢这个故事的原因,因为它证明了这里的学生真的不只是普通的大学生而已。如果你不是一个敢于冒险的人,你是不会来这里的。即使你在上海长大,来这所学校就读也是一种实验和冒险。所以这群学生挑战成功了,我不应该感到惊讶。同时,这所学校也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群体。这个实验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这所学校的独特之处,尽管我觉得校长Jeff Lehman一定对我很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