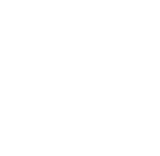你在这里
上海纽约大学新校务长衞周安
请简单介绍一下您自己。
我从1992年开始在纽约大学教授中国历史。从2009年到2012年,我担任了纽约大学历史系的主任。我也参与了阿布扎比纽约大学的建设,主持设计了历史课程,并帮助聘请了学校最早的三位历史学家。我还在上海为授过阿布扎比一月寒假课程授课,与纽约大学全球教育体系里的学生们也有密切的联系。基于以上的这些原因,以及从自身专业出发对中国的兴趣,我被邀请来担任上海纽约大学文理学院的创始院长。
您为什么选择研究中国,您对中国的兴趣点是什么?
在我18岁毕业的时候,在大学这四年里,我就下定决心,要做那些我一辈子再也没有机会做的事情,所以我选择了学中文。这真的改变了我的一生。四十年前,我第一次来到中国,那是1973年,我在这里待了一个月。那次经历深刻地改变了我的世界观。我们坐了9天火车,从伦敦穿越西伯利亚来到中国。那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后几年。遭遇到的都是从来没有经历或听说过的事情。这段经历,无疑奠定了我对中国的兴趣,尽管作为历史学家,我的研究专业是很多年前的中国。
您对中国历史的哪一段最感兴趣?
17到18世纪的清朝,是18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王朝之一。那时候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开始多了,而我对于那时候的中国与外界的关系,很感兴趣。而用两极化的“里”和“外”的概念来讨论这些关系,就有点过于简单化了。
我还对贸易以及中国与外国的艺术、科学和宗教的交流感兴趣。我喜欢研究各种层面上发生的事情,并着意研究这些事情怎样不经意地影响着当时人们的生活。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题目是“十八世纪的中国法律”,因为我之前当过律师。最近,我的学术兴趣也在慢慢返回这个话题。另外我也非常喜欢中国的饮食文化。
在您的研究里会不会常常比较中国的现在与过去?
不太多。要说“这个现象跟200年前是一样的”这样的话,简直太容易。然而,语境是截然不同的。有时你可以看到一些回应或线索,但我觉得太多的对比现下与过去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因为事物总是变化的。
在课堂上会不会给学生们讲很多关于您在中国经历的故事?
我会给学生们讲故事。有时候告诉他们“我刚来这里的时候,浦东还不存在,只是一片沼泽。” 我也告诉他们四十年前第一次来中国的经验。那时候所有人都穿着灰色的中山装,所以来之前我们被嘱咐不要带裙子。我被告知说,“中国所有的女人都穿裤子的”,我们就只带了裤子。到了乡下发现所有女人竟然都穿着裙子!她们就问我们,“穿裤子不热吗?干嘛不穿裙子呀?” 我会跟学生们讲一些这样有趣的琐事。
您的个人使命是什么?什么东西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
可以说我的个人使命就是做一个真实厚道的人,这最重要。我也想在每个情况下尽量做出适当的选择。有可能因为我研究中国研究了很久,我真的觉得应该时时刻刻尽量做到互惠这一美德。我觉得这是我从孔子学里面所体会到的最深刻的一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另外我还觉得很多事情和现象之间都存在着你意想不到的联系,我们应当努力地探索这些联系。
您怎么看我们的这些学生?
他们很棒。有时想想,他们当时能够下定决心来上一个根本还没有建立的学校是间非常了不起和勇敢的事情。他们有机会在零基础上帮助建立一所学院,这是非比寻常的一件事。有时会突然想起他们其实只有18岁,有很多事情他们还不了解。但是他们很用功、用心、真诚,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一年里看着学生们的成长,真的令我为他们骄傲。他们的成长出乎了我的预料,他们的语言能力、自信和成熟,简直让我惊叹。西方的学生和中国学生慢慢开始融合并在一起。我们在理论上设计学校,而他们——我们的学生在实践并实现着我们的设计,让我们的梦想渐渐成为现实,这的确令人兴奋。
您对上海纽约大学至今的进展哪些方面比较满意,哪些方面觉得需要提高?将来学校会怎么发展?
有点不敢相信,第一年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觉得总体上走得稳健。当然,我们也会犯错,我几乎每天都会发现可以改善或者修改的地方,但是有时牵一发会动全身,改变一件事情就会影响到别的所有地方。
在这一年里我们进步了很多。我们的沟通越来越好了,我们更加了解别的部门在做一些什么事情,也在规划上改善了许多。我们和学生的沟通越来越多。我每周都会请一起喝茶,了解一些他们关心的事情。他们在学术上如果遇到问题就来找我, 如果在生活上遇到困难就去找Tyra Liebmann (上海纽约大学学生事务院长),我跟Tyra几乎天天都有交流,所以我们充分把握着学生们的观点。
找到平衡,是一件极微妙的事情。教育并非消费者主导一切,教育也不该被视为一种消费活动。学生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而每一个建议我们都会认真地去考虑。有时候会觉得他们的想法是正确的,但也有时候,事实上,我们感觉比他们更懂得因该怎么去教育、给他们提供哪些方面的资源。这是一个颇具创造性的互动过程。上海纽约大学还很小、很新,这也是这所学校的优势,我们可以做很多大学院做不到的事情,也很容易做调整。
作为教务长,您负责构建学校目前和将来的课程,您对未来的课程有什么看法?
目前我们规模还很小,所以教授还没有被分配到各个系,所以我们享受着多学科间密切沟通交流的乐趣。在纽约我几乎不认识其他系里的教授,而在这里我天天有机会和理科教授谈话,还包括别的学科里的教授们。我们每周举办的研讨会会吸引许多人,历史学家有机会听到物理学家的演讲,科学家有机会听历史学家讲话,等等。这是相互促进智慧的绝好机会。
我们希望建立一所跨学科的大学。我们将会聘请一位科学哲学家,让哲学和科学紧密联系。在这里,经济学者和神经科学学者互相影响、文学家和社会学家也有交流。如果我们可以在学校的成长过程中保留这些跨学科的联系,上海纽约大学的课程将会是非常独特的。
如果资金不成问题的话,你对上海纽约大学有怎样的愿景?
我会为学生们提供机会去各种地方做一些有趣的事情。虽然现在的世界已经全球化,而能够通过亲身经历去体会别的文化,并得到启发,才是与学术并重的重要东西,这是一种不可替代的学习机会。我很希望将来可以给我们的学生更多这样的机会。
今年春假期间,我们从研究经费中拨出了一笔资金,带领两组学生去了中国两个不同的地区参与义务劳动。一组去了四川,做仁爱之家的志愿者;另外一组去了云南,帮助受艾滋病毒影响的家庭。许多参与了这些项目的学生写信告诉我,“这是一次非常棒的经验,我还想参与更多。”
其实,我真正想要的是更多时间。我们有太多想做的事请,一天24小时实在太少了。但是唯有时间是无法买来的。